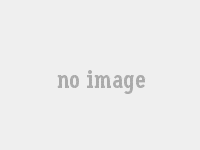英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吗?(Of Language)
思忖良久,犹豫再三,要不要写下浮现在脑海中的些许所思所想,唯恐这些来之不易的感悟慢慢消逝,或是随着时间渐渐变质。我原本没有想要洋洋洒洒敲出千多个字,想着是不是就发个微头条随性记录一下便可,但真正开始创作码起字来,竟不免地想多“挤”出点什么来,连(这一段)语言似也稍也多了几分不知恰当与否的“矫揉造作”,以至于写到这里还在写些似有似无的“前言”,以至于思忖良久前原本的“我”都被删去—— 好像这样能达到某种若隐若现的“效果”一般,以至于此刻不免开始怀疑这篇所谓的文章是否能恰当地呈现。应该还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写点什么东西,所以便写点什么,然而囿于时间、精力等,我也不想写得太麻烦,不至于还得大费周章地搜索一番信息。
有时在网上看到网友在争论英语和汉语哪个更加“先进”,当然大多数人都还是不假思索地一个劲地夸耀母语的博大精深,我也很欣慰看到至少大家一致的态度是这样,但其中不少言论就似乎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对英语的贬低了。这就让我想到了涉及这个话题的一个经典“双标”评论: “如果一种表达汉语比英语更加丰富精妙,那就是汉语博大精深而英语浅陋粗俗;如果一种表达英语比汉语更加意味深长,那就是汉语更加简洁高效而英语冗长复杂”。我觉得可能一个比较切合的例子就是月份和星期? 有人说,英语的每个月份和星期多难记,“January,February,March,April; 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 …”,不像汉语直接“一月,二月,星期一,星期二”这样数下去,于是得出结论:英语复杂无益,低质低效。我这里不想去谈英语月份与星期背后涉及有趣的历史文化,也不想去考究古代汉语中对月份星期的所谓雅称别称以及这些称呼流变的历史渊源和实际应用情况。再比如,随便拿出一句汉语诗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或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怼着让拿出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能完全表现出此种精妙的对应的英文翻译,最终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英语完全比不上汉语,汉语博大精深,英语翻译用词简直俗不可耐。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有关于一首名叫“你说你喜欢雨”的英文诗翻译。英文原诗很简单,以至于不少人看着觉得“低级”。这首诗中文翻译给出了很多很多版本,有“诗经版”、“楚辞版”、“五言七言律诗版”等等。且不论翻译的信达雅如何或“是不是有点添油加醋太过了”,我看着确也佩服网友们的才华和母语丰富的表现力,但最终讨论往往聚焦到对两种语言的“拉踩”了。面对那么多版本的高雅而精巧的中文翻译,一首简单的英文短诗确实显得单薄而俗气了。

《你说你喜欢雨》的例子

像这样的例子确实是数不胜数
以上这种例子确实是太多了,也都太片面太偏颇了,且从头至尾透着一种由无知而产生的优越感。譬如上面这个“wife”的例子,且不说他/她有没有具体考究英语中妻子的各种叫法,只是一个劲把汉语中关于这方面的各种雅称敬称谦称俗称甚至于把“皇后”这种基于具体关系情景的称呼搬出来,然后甩出一句“而英语就个wife”,仿佛形成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对比。完全抛开具体文化和语境,完全忽视语言的逻辑和内涵,只是为了“拉踩”而“拉踩”了。
我也确实看到有很人指出英语的一些精妙和先进之处,其中不少很有启发。有一种观点非常巧妙,我也深表赞同,大概意思是说语言只是服务于实际使用需要,在这里我也想随便提几个例子。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是关于爱斯基摩人“雪”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真实性可能有待考究,不过也能反映很多问题了。爱斯基摩人常年生活在冰天雪地里,据说他们的语言中有关“雪”的语汇达数十种之多,有按时间分类的雪,有按形状分类的雪,甚至有按踩上去的质感分类的雪,等等。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雪”是他们生活中常见的东西,他们的日常交流中也不免要经常用到,于是他们对各种各样的雪一一赋予对应词汇,发展出了如此丰富的关于雪的语汇。还有英语学习者经常表示不理解的英语中“动物分公母(甚至大小)”和一些“禽肉分离”的现象,比如“chicken(鸡),hen(母鸡),rooster/cock(公鸡)”,“deer(鹿),doe(雌鹿),stag/buck(雄鹿),hart(雄鹿,尤指雄赤鹿),hind(雌鹿,尤指雌赤鹿),fawn(不足一岁的幼鹿)”,“horse(马),colt(四五岁左右的雄马驹),filly(幼年雌马),foal(小马驹),gelding(阉割过的马),mare(母马),stallion(种马)”,“cattle(牛),ox(阉割的公牛),bull(公牛),cow(母牛,奶牛),bullock(阉割的小公牛),calf(小牛犊),heifer(未生育过的小母牛)”,以及各种肉:beef(牛肉),pork(猪肉),mutton/lamb(羊肉),venison(鹿肉),veal(嫩牛肉)等等。如此区分,想必是他们在畜牧业上确实有实际需要,慢慢就反映到语言中了,而出现各肉类的名词,则是跟当年诺曼征服的法国贵族有关。这些肉食名称全部来自法语,享用肉食的是上层社会的讲法语的贵族,这些贵族觉得古英语词汇的声音不雅,因此当这些肉食被端到贵族餐桌上的时候,便有了法语名称。所以,从这方面指责英语词汇的繁琐低效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汉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是很大程度上过时了,或是在长期使用母语中很容易慢慢察觉不到了。比如汉语词汇中对于马的分类: 驳(bó):毛色不纯的马;馰(dí):额白色的马;骧(xiāng):后右蹄白色的马;馵(zhù):后左脚白色的马;騴(yàn):尾根白色的马;骢(cōng):青白色的马 ……如此种种,数不胜数。再比如有关“牛”的字: 犊(小牛)、牝(母牛)、牡/牤(公牛)、犙(三岁的牛)、犗(阉割过的公牛)、犤(矮小的牛)……各种分类,不胜列举。马和牛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社会里,牛是必不可少的家禽; 马则奔驰各个驿站之间,传达政令,远送家书。正是因为当时有必要,先民们才会创造出这么多有关它们的字。

还有一种经常在网上看到的说法:英语几乎要为每出现的一件新事物造一个词,其词汇量会无限膨胀,反观汉语则只需要将原本已经存在的字排列组合即可适应需要,由此觉得英语低效而必将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这种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混淆的英语中的“词”跟汉语中的“字。如果我们类比一下,汉字的笔顺跟英文26个字母相似,而汉字中虽然有些一个个的单字足以表述清楚某些意思,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它是不能完全等同于英语的“单词“的。譬如“tennis(网球)”,汉语中是不是还要将“网”和“球”两个单字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词呢?“网”字以概括出基本特征,而“球”字以表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字的“字”同英语的“词根词缀”类比更为恰当。比方说,“gramophone”(留声机)是由词根“gram(o)”,意思是“to write(写)”和“phone”,意思是“sound(声音)”组成的,字面含义就是“写下声音(的机器)”。再比如汉字中的“化”字,可以用在形容词或名字后表示某种状态或性质的变化,如“现代化”、“城市化”等等,对应的则是英语的后缀“-iz(s)e”,如“modernize”、“urbanize”等等。再如汉字“然”,可以用于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表示“什么什么的样子”,如“诚然”和“飘飘然如遗世独立”,这可能则对应英语的词缀“-ful”。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汉字的表意功能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然而再引进或创造新词的过程中,汉字的表意功能却存在被“剥夺”了的情况,如“克隆”,纯粹是“clone”的音译,无法从字面看出其“复制”的含义,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由于四处借词等原因,英语是一门词汇量极其巨大的语言。据统计,发展至今,英语一共从100多种语言中借过词汇。原本英语中已大概有相近意思的词汇,又从法语和拉丁语中借,结果就是英语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同义词,这就使得其表达不断精细化,一组表达相近意思的同义词,每个词却又有非常细微的涵义。“英语中没有任何一组同义词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在某些方面,英语一定能比汉语更精确地表达,同样地,汉语也一定在某些方面能比英语更精确地表达,这只是跟各自的文化历史等因素有关罢了。在漫长的殖民和全球传播过程中,英语还借用或形成了很多十分具有本土化气息的词汇,如bazaar(中东的集市)、vizier(旧时某些穆斯林地区的高官)、wigwam(旧时印第安人使用的圆顶或锥形的棚屋)、boomerang(回旋镖,最初是澳大利亚土著用于狩猎的器具)等等,这些都使得英语在某些方面的表达或氛围营造上十分精妙。
英语词汇量之庞大,世界上其他任何语言难以企及,而能与之一较的可能就只有我们的博大精深的汉语了。英语出身卑微,发展历史不过一千六百年左右,但由于殖民扩张和四处借词等原因,形成了庞大的词汇量。而我们汉语历经数千年发展,在这期间既有独立发展,也有向其他语言借词,其词汇量足以与英语匹敌。近代以来,汉语越来越收到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影响,汉语中已经充斥着英语借用词和借用语,这甚至可能是以一种已经难以被轻易察觉的方式。明显点一眼能看出来不原本属于汉语的,可能是“芭蕾”、“克隆”、“麦克风”之类的词汇。较难看出来的,有如“电话”(telephone)、“蕾丝”(lace)、“脱口秀”(talk show)之类。其中“电话”之类的词汇,主要是由于进入汉语当中已经太久以至于慢慢融入了进来,而“蕾丝”和“脱口秀”之类我个人觉得则主要是因为翻译得太过巧妙,“形神兼顾”,音近似的同时又发挥了一定程度上汉语的表意功能。还有一类最不易发现的借用语,就是诸如“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冷血动物”(cold-blooded creature),“以眼还眼,以牙还牙”(an eye for an eye,a tooth for a tooth)等等。有人可能会感到不解,这些不是都是汉语中非常常用的表达吗,怎么都来自于英语了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些表达太过于融入,我们才渐渐地意识不到了。可以这么说,这些表达都不是汉语中独立发展出来的,换言之就是没有从英语中借用这些表达之前汉语里“根本就不会这么讲”。以上面的“population explosion”为例,“explosion”在英语中除了“爆炸”的本义外,还有“激增”之义(a large,sudden or rapid increase),但当时在翻译“population explosion”的时候,可能还是直接译成了“人口爆炸”而不是“人口激增”,于是汉语中“爆炸”一词也多少带了些“增长”的意味,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爆炸式增长”一样。这再往深处去想,我想是不是就跟人类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的初始逻辑有关了,实在耐人寻味。汉语从英语中借用的各种词汇和表达,同样细化了汉语的表达功能,使汉语能更为准确生动地传达某些方面的意思。
我曾苦苦思考一个问题:语言的美感是如何产生的?读到一首优美的唐诗宋词或是篇优美的散文随笔,我惊叹于汉语丰富的表现力。而在当时的水平下,看到一些英语的对应翻译之类的,却无法感受到其中的美感。现在,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随着知识和水平的精进,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些初步而浅显的认识。我想,本质上还是表达如何丰富如何形象的问题,这其中我还有太多太多没有思考到了。读到一些英语文学作品,我深深折服于他们对于这种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其表达之精妙形象,其思想之深刻洞见,而反思自己对于母语的“驾驭能力”则还远远不够,现在一度觉得自己的汉语词汇量也太过匮乏,我对这两种语言都了解得太少太少了。似乎不太恰当地借用牛顿的名言,“我只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海边玩耍的孩子,有时为找到一块光滑的石子或美丽的贝壳而兴高采烈,但真理的海洋仍然在我的前面未被发现”,只是我捡起的“贝壳”可能远没有那么“值当”。
我无比庆幸自己的母语是汉语,如此博大精深的汉语,让我可以用母语的视角去体会它的美。我愿意相信汉语是最好的语言,但我绝不敢轻视人类历史上的哪怕任何一门语言。语言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本质上来讲语言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我们现在将英语视为比汉语低劣的语言,可知当年日不落帝国的时代,当年英语正在全球范围内迅猛传播的时代,有多少讲英语的人和大“语言学家”觉得英语优于世界上一切其他语言呢!在他们看来,英语是圣经的语言,是上帝的语言,是乔叟和莎士比亚写作用的语言。我不仅想起最近一个英语演讲话题:“Prejudice is the child of ignorance”(偏见是无知的孩子),我们当以平和包容的心态去了解和学习其他语言文化。
最初看到太阳给它命名“日”,感到高兴将这种感觉称为“高兴”。语言从最初几个原始人嘴里的咿咿呀呀走到现在,其能表达的背后的丰富的思想和观念已经令人赞叹不已。然而这还不够,除了各种语义和观念上的限制,还要形象,还要有各种技巧和修辞,诗词还要有严格的韵律。诗人作家用语言就像戴着镣铐跳舞,还能把这舞跳得如此精彩绝伦。还有语言那“音义相关性”,又揭示了怎样奥妙的语言逻辑呢?
只是有感而发,时停时写,时写时停,颇有“想到什么写什么”的感觉,只是走马观花,很多东西没有讲清楚(可能也暂时讲不清楚),但所幸本身就是打算随便谈谈,记录记录感悟罢了,所以勉强叫“Of Language”? 记得高中生物必修一教材分子与细胞的大概第三章(记不清了)介绍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前面的引言下面有好像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我坚信即使是自然界中结构最为简单的细胞,也要比人类目前为止设计出来的最先进的计算机更为精妙。那么人类创造出的最精妙的东西是什么呢 —— 最后我想以这么一句话结束: 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精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