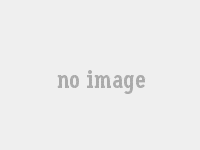胡服盛行与女着男装——论唐代前期服饰风尚与女性社会地位关系
胡服盛行与女着男装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大特色,并被不少学者视作唐代社会开放与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唐代社会之开放包容,堪称中国历代之最,学术界对此已有共识。但胡服盛行与女着男装等服饰风尚是否就是唐代女性意识觉醒、女性地位提高的标志,以及唐代女性是否具有超越其他历史时期的更高地位,却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近年来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孙机先生就不赞同着男装与着胡服是“女权意识的某种觉醒,也是对传统的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的说法,认为“着男装着胡服并非唐代女装的主流”,“云想衣裳、髻簇珠翠,仍然是唐代上层妇女的追求与向往唐朝服饰图片,而男装和胡服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此外,不少论及唐代女性服饰的文章,大都有意无意地将“初唐、盛唐时期的女性”与“整个唐朝的女性”混为一谈,忽略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动态变化。事实上,从社会史和服饰史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时段唐代女性的形象、活动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尽管对唐服饰发展的分期还可以进行讨论,但不论怎样分期,服饰在不同时期应是各具特点而又脉络分明的,机械地、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显然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针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陷,通过重点探究以安史之乱为节点的唐代前期女性服饰与其社会活动的动态变化,来揭示唐代服饰风尚所反映的“女性地位”“女性意识”,从而为唐代的女性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 图一 唐代陶俑中的女着胡服形象
1. 陕西咸阳杨谏臣墓出土的彩绘胡服女立俑2. 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胡服骑马女俑
唐代胡服与男装的流行和消逝
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唐代的服饰风格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从总体上看,安史之乱前的唐代前期女性服饰,在承继北朝、隋代传统服制的同时受到西域、北方游牧民族风尚的影响,包含了更多的胡风元素,体现了胡汉交融的特点。
无论是考古出土实物资料还是文献资料均表明,女着胡装和男装流行于唐代前期,安史之乱后骤然减少。而以武则天为首的女性政治集团的活跃期也正好与这类服饰的流行时间相吻合,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更加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女着胡装和男装流行与唐代女性政治集团的活跃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着胡服是唐代前期女子的服饰流行风尚,更是传统视角下,唐代风气开放、女性地位较高的标志。胡服,目前普遍认为是除汉族之外的所有少数民族服饰的统称,也包括波斯、印度等域外服饰。其特点是上身多着窄袖紧身袍或短衣,腰间系革带,下身着长裤和革靴,便于劳作和活动。
胡服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此后的各个时期均有记载,但最流行的时期显然非唐代莫属,因为在唐代不仅男子着胡服,还出现了女子着胡服的现象(图一)。根据沈从文先生的研究,其流行时间大致在开元、天宝年间。但从初唐新城长公主和房龄大长公主墓壁画中均有身着胡服的侍女形象来看,其流行时间应当是初唐至盛唐时期。
唐墓壁画中所出现的胡服侍女形象,衣着大致为袖口较窄的圆领或翻领长袍,长度大致在膝盖以下,再配以条纹波斯裤,穿透空软棉鞋,头戴锦绣尖锥形小帽(图二),与西域地区的胡服卡弗坦形制类似,应是受西北民族和波斯诸国服饰影响的结果。除衣着外,唐代妇女的首服中也有不少胡风元素。
如从初唐武德年间至中宗后流行的帷帽(笠帽)就是从“戎夷”的“冪䍦”发展演变而来的。“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冪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有惟帽,拖裙及颈,渐为浅露。”“中宗后……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冪䍦本是胡、羌民族的首服。
因西北地区多风沙,女性多用冪䍦来遮蔽风沙侵袭。传到内地后,其时髦新潮的外貌与儒家“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封建意识相吻合,冪䍦的功用就由防风沙变成以防范路人窥视妇人面容为主,并很快成为唐朝妇女喜爱的装束。陕西礼泉郑仁泰等墓出土的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等考古实物也证实了笠帽的流行情况(图三)。


▲ 图二 房陵大长公主墓出土的着胡服托盘提壶宫女图
胡服在唐朝流行的原因,一方面是南北朝以来胡汉民族文化交融与流变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统有关。陈寅恪先生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
天生的异族血统和固有的胡人心态使李唐皇室对所谓的“华夷之辨”相对淡薄,而对胡族习俗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其中统治者对胡舞的垂青是当时胡服流行的直接原因。“在以皇室为中心的宫廷主导文化强大辐射力影响下,贵族女性从对胡舞的喜爱发展到对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服的模仿,从而使胡服在唐代迅速流行”。对此,唐诗中多有反映。如元稹诗《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当然,胡服在唐代流行的深层原因还在于胡服“不受唐朝礼法的约束,服饰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无须琐细地区分尊卑身份,因此穿胡服既不受越级僭用的刑法管制,又不受背离纲常名教的指责,故长安虽没有异族入侵用屠刀逼令人们改衣胡服的情况,但新的服装观念敏锐而迅速地渗透入市民的思想,人们普遍喜欢穿戴胡服”。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胡服“不仅形式独特新颖,而且相对比较贴身,有利于突出女性身体各部分的曲线,因而具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 一个时代的潮流风尚多半会受到政治、经济及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唐代,胡服的逐渐消逝直接与“安史之乱”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有关。
“安史之乱”后,人们在反思战乱原因时,根据天人感应说,认为此前胡服的流行不仅是战乱的征兆,更是引起战乱的原因之一,即《新唐书·车服志》所称“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出于对战乱原因的反思以及对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的厌恶,安史之乱后,华夷之辨更被强调,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排斥胡服的风潮,“胡服”热逐渐降温,胡服的穿着频率大幅下降,中华宽衣博带之传统重新回归。
但“安史之乱”时,由于唐肃宗借兵回纥平定叛军,之后大量的回纥人留居在唐朝境内,因此又在女子服饰中短暂兴起了回纥衣装。宋代,由于契丹人的势力逐步强大,对宋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为防止“胡风”蔓延,宋朝曾多次颁布禁令,禁止民间效仿胡俗着胡服。至此汉人统治阶段的胡服风尚正式结束。


▲ 图三 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
在胡服的影响下,“女着男装”也是唐代的一种流行风尚和唐代女性服饰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无论是唐以前还是唐以后,“女着男装”均被中原王朝统治者视为一种“异端行为”。尽管唐代女穿男装流行,但在宋人编撰的《新唐书》中,依旧用“服妖”这一极度批判的话语来评价这一现象,而这种看法却是后晋刘昫《旧唐书》中所没有的,这也体现了“女着男装”现象之于唐代的特殊性。
从《新唐书·五行一》中“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的记载看,即便在唐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女着男装”也并非真心接受,或者说,在唐代地位较高之女性是不宜着男装的,只有地位较低的杂役宫女才会穿胡服穿男装。
如唐代薛逢的《宫词》“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意思是无宠的嫔妃羡慕穿着袍袴男装的宫女可以为皇帝扫床。“袍袴”在唐代是男子衣冠,特指男装女性,这一点在孙机先生《唐代之女子着男装与胡服》文中已有专论。 而“女着男装”能流行唐朝,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频率的增加以及骑马出行成为普遍方式,传统的女性服饰不适合或者不便于骑马,女性出于对骑行的需求,选择穿着简便的男装。
二是受到外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唐初诸多制度、习俗都承袭了隋朝,而隋朝则脱胎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同时长安又是帝国的商业中心,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其服饰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唐朝人的风尚。
在房陵公主墓中,便出现了很多“女着男式胡服”的壁画,例如前甬道西壁的两幅侍女图、前室东壁南侧的侍女图及前室西壁的侍女图,几名侍女都身着粟特式的男装,正是这种文化影响的一种体现。 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女着男装的风尚也流行于唐代前期,尤其以武周时期为盛,而安史之乱后逐渐减少,唐以后基本消失(表一)。
表一 考古发现所见女着男装图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献记载中屡屡提及胡服在唐代各阶层流行的情况,但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却与文献记载不尽一致。如陶俑中着胡服或男装的女子多为宫廷侍女或家内侍仆,少见身份高的女性。唐墓壁画中穿袍绔、翻领胡服的女性,大多居于着裙衫者之后、队列的中部或后部,身份显然较低。从未见过由袍袴或着胡服的女子牵头的(图四)。唐墓壁画中胡服女性身份主要有侍女(宫女)和乐舞伎两类。
在太子、公主等皇族墓中着胡服或着男装袍袴的女性应是宫女,出现在一般大臣墓中应是侍女。侍女或宫女一般是手持各种物品以表示为墓主提供某种服务,手中不持物的胡服宫女和侍女可能表示待召唤。
唐墓壁画中的穿胡服女乐舞伎不多,不少是胡女,而且舞蹈服装保留了胡服的样式。总之,考古实物中所见着胡服或男装的女性多为身份较低人员的现象说明,因胡服便于劳作和活动,主要流行于社会的下层,并非唐代女装的主流,与女性政治地位之提升似乎没有关系。


▲ 图四 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
胡服男装与骑马外出活动——服饰风尚的变化和社会活动变化的不对等
服饰风格往往被视作社会风气、风俗的表象。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服饰的特点与人群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地位相联系,许多学者将唐代前期独具特色的袒露装、胡服、男装作为女性地位较高的实证似乎也不无道理。
从长时段看,唐代以安史之乱为界,形成两种迥然相异的服饰风格。而以唐前期的短时段来看,在安史之乱以前,又以武周时期为界,呈现出一种变化鲜明的动态过程。袒露、胡服、男装等为世人视作唐代女性地位较高标志的服饰元素,皆于高祖、太宗之世就已出现,到武周时代趋于顶峰,到开元天宝年间已出现异化和些许衰落,而安史之乱后更是日渐消逝。
基于上述认识,人们将简约实用、袒露胸乳、胡服男装作为唐代女子地位之高的证明,似乎有意或无意的指向这样一种观点:唐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是随着武周时代的兴起而提高,又随着武周时代的衰落而走向低迷,而对这些社会风尚出现的原因,则归因于唐代的对外开放和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女性的政治成功。
但问题在于,上述几种服饰元素虽然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但是其流行和消失的大致时间是不完全一致的。简约实用的服装风格往往与骑马等社会活动相联系,但在女性骑马盛行的武周、玄宗时代,服装已经由简约转变为繁奢,袒露装武周时期盛行,但却缺乏进一步的史料说明其影响,而胡服与男装的流行和消失则更多的受安史之乱影响,这些元素能否共同作为唐代女性地位较高的例证?
仅仅简单的将服饰元素的流行与这种关于唐代女性地位的笼统印象划上等号,显然是不够严谨的。实际上,从胡服和男装的变迁中可以看出:服饰的变迁往往与社会变迁不对等。
文献中关于唐代女性外出活动的记载很多,女性外出的活动又往往与节日相关联。“上巳祓禊”是唐代一个重要的节日,从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诗句可以看出,每年“上巳节”都会有大量长安城内的女性前往水边开展祈福活动。与之相类似的其他节日唐朝服饰图片,往往也都有女性外出的身影。
中宗以后,“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说明宫廷女性骑马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此外,唐朝的贵妇也经常骑马出行。《明皇杂录》卷下记载“虢国夫人每入禁中,常骑骢马,使小黄门御。”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一副描写虢国夫人骑马出游的作品。这幅画作同时反映宫中女性外出着男装胡服的现象,画中最前方的男装女子更是被许多人认为是虢国夫人。
文献中对于女性骑马外出着男装胡服同样有许多记载。另外,唐高宗以后女子骑马外出常用的遮盖面容的冪䍦也出自胡人。这些例证共同说明外出活动与这种服装风尚的关联性。不难看出,胡服男装既是女性外出活动的轻便选择,也是异域文化影响下的自然结果。那么,在安史之乱后,胡服与男装逐渐消失,女子的外出与骑马是否受到影响?
答案是否定的。如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北壁下层的《宋国夫人出行图》所描绘的唐朝末年河内郡一位贵妇人宋国夫人骑马出行的盛大场景,说明即使到了晚唐,女子骑马出行仍然是被允许的。从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
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抱鞍桥。”“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盘凤鞍鞯闪色妆,黄金压胯紫游缰”等诗句,也说明晚唐、甚至五代,女子骑马的现象仍然存在。骑马之事既然未绝,而女子的节庆外出同样未有太大变化:长庆元年二月,太和公主“暂驻受百僚之谒见,士女倾城观焉”“僖宗皇帝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然京城耆耊士女,争为送别”。
说明到中晚唐时,官方礼佛一类的重大社会节庆,公共场合依旧少不了女性参与。因此,同样可以推断,尽管胡服和男装的流行与女性骑马参与公共社交活动有着种种联系,但其本身并非女性地位较高的例证,因为与其直接关联的社会活动——“骑马”本身不因其存废有变化,男装或者胡服,说到底,只不过时唐初与盛唐时期,在丝路未绝、胡风盛行年代的文化表象。
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社会风气的开放对女性的影响,但当安史之乱结束,中原开始厌弃胡风之后,它随着胡风的不再流行而消逝,但早已存在的社会活动却依旧保持。
结 语
胡服盛行和女着男装是唐代前期妇女服饰的一个独特景象。从胡风元素在初唐女性服饰中的承继发展,到纯粹由丝绸之路带来的胡人服饰的盛行,再到安史之乱后胡风元素逐渐消失,这一景象和过程体现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文化的交流融合、唐人开放包容的社会心理、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以及唐代女性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政治事件、民族关系对潮流风尚的影响。
但从其仅流行于安史之乱以前以及主要流行于身份较低的阶层看,显然无关乎唐代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挑战,无关乎女性社会地位之提升,因此不能被视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
不过,由于唐代历史的特殊性,尤其是女性政治家短暂的活跃,人们仍然可以对这一独特景象所反映的唐代开放包容的社会感到一种由衷的钦佩和赞叹,如同爱德华·吉本出于对于罗马帝国的追思,去肯定这种建立在文化的开放与交流之上的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