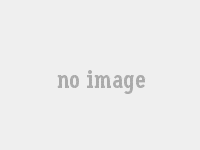吕博:唐西州前庭府卫士左憧憙的一生
天下惡官職,不過是府兵四面有賊動,當日即須行有緣重相見,業薄即隔生逢賊被打煞,五品無人諍[1]——《王梵志诗·天下恶官职》唐代府兵制度一直是中外唐史學者十分關心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唐長孺、岑仲勉、谷霽光、張國剛、孫繼民、孟彥弘、熊偉以及日本學者濱口重國、菊池英夫、谷川道雄、氣賀澤保規等学者對唐代府兵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經過學者們的努力,唐代府兵制的基本制度構成、運作情況已經基本明晰。
[2]不過,儘管我們對於府兵制度內涵認識日益清晰,卻幾乎不知道府兵制度下任何一個唐代衛士個體的生命歷程如果從史料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會發現關於唐代府兵制度性規定的條文,史書中保留下來不少,卻鮮有史料具體描述府兵制度下個體兵員的生存狀況。
幸運的是,吐魯番阿斯塔那四號墓中的有關唐西州左憧憙的墓誌、文書,為我們瞭解這方面的情況,提供了珍貴材料這些材料,已有不少學者著重從某一角度研究利用過,有的注重西域邊防,[3]有的利用契約文書研究西域地區的社會經濟情況。
[4]而本文將注重左憧憙的府兵生涯,試圖將這些文書、檔案等零散的材料串聯成敘事,復原一位原本在歷史時期籍籍無名的府兵些許生計、生活的樣態有時候為了理解左憧憙的一些行為,本文将利用《木蘭詩》《王梵志詩》等涉及唐代府兵、百姓日常生活的材料進行補充论述。
一財豐齊景與左憧憙的府兵身份因為當時發掘條件的限制,左憧憙墓葬的詳細考古信息,今天所知甚少但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應當是他的墓誌與十五件借貸契約其中142字的墓誌大致勾勒了左憧憙的生平:維大唐咸亨四年(673),歲次甲乙(戍);五月丁未朔廿二日。
西州高昌縣人左公墓志並序君諱憧熹,鴻源發於戎衛,令譽顯於魯朝德行清高,為人析表財豐齊景,無以驕奢意氣陵云,聲傳異域屈身卑己,立行修名純忠敦孝,禮數越常以咸亨四年五月廿二日卒於私第春秋五十有七,葬于城西原,禮。
嗚呼哀哉!启斯墓殯[5]據墓誌可知,左憧憙生於616年,卒於673年他一生經歷了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其主要活動則屬唐高宗統治時期從相關文書得知他是西州高昌縣崇化鄉人, 身份是前庭府衛士誌文雖然用典,但都較為淺顯。
誌文所謂“ 鴻源發於戎衛” 的“戎衛” 二字,似應指他當府兵的生涯而言下一句“令譽顯於魯朝”似乎在暗示他是左丘明的後裔在左憧憙的墓誌中,我們看到另一處借助典故進行的評價,說他“財豐齊景”《論語》提到齐景公说他富裕,有馬四千匹,死的時候,百姓們覺得他沒有什麼德行可以稱頌。
而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下,百姓們到現在還在稱頌他們墓誌誌文十分扼要,如果不結合墓葬內的契約等文書,我們對左憧憙生平相關的信息,還是知之甚少財豐齊景的程度,左憧憙應該達不到不過,從放貸、買奴、租菜園等商業活動來看,他平時善於經營,生活理應比較富裕。
墓中紀年最早的一件文書是《唐顯慶五年(公元六六〇年)張利富舉錢契》:1 顯慶五年三月十八日,天山縣南平2 鄉人張利富於高昌縣崇化3 鄉人左憧憙邊舉取銀錢拾文,4 月別生利錢壹文到左還須5 錢之日,張即須子本具還。
若身6 東西不在,一仰妻兒及保人等7 代;若延引不還,聽掣家資8 雜物平為錢直兩和立契,9 畫指為信10 錢主11 舉錢人張利富12 保人康善獲13 知見人[6]天山縣南平鄉人張利富向左憧憙的借貸契約屬私契,按照唐王朝法律規定:“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官不為理。
”[7]我們不清楚顯慶五年唐政府規定的利息,但從開元二十五年前後政府的詔書來看,[8]張利富向左憧憙借銀錢拾文,月息達百分之十,顯然屬於高利貸在契約第12行,我們看到了一位康姓的粟特人擔當了張利富的保人。
西州在當時是東西方貿易的樞紐,有大量粟特商人往來、定居,商業氣息濃厚顯慶五年唐王朝改元龍朔,在唐高宗龍朔元年(661)五月的一件契約中,可以看到左憧憙的另一個身份前庭府衛士他在柳中縣五道鄉蒲昌府衛士張慶住邊買了一名奴隸,這也表明他在做一些販賣人口的生意。
買奴契具體內容如下:1 龍朔元年五月廿三日高昌縣崇2 化鄉人前庭府衛士左憧憙,交用3 水練陸疋、錢伍文,柳中縣五道鄉蒲4 昌府衛士張慶住邊買奴壹人,5 字申得,年拾伍不奴及6 練到日交相付7 叁日得悔,
8 者,壹仰9 為信。[9]契約中出現了西州折衝府蒲昌府的最早記録。無論是左憧憙所在的前庭府,還是張慶住所在的蒲昌府都是西州的軍府。同樣在這一年,我們看到左憧憙於同鄉人大女呂玉邊租佃菜園一所:

唐龍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左憧憙夏菜園田契1 龍朔元年九月十四日,崇化鄉人左憧憙2 於同鄉人大女呂玉邊夏張渠菜園肆拾3 步壹園。要逕(經)伍年,佃食年伍。即日交4 錢

(捌)文限一年,到九月卅日與伍文5 十月十6 錢半文,若滿依7 □園□滿,一罰三分園中渠破水讁,仰8 治園人了;祖(租)殊(輸)伯役,仰園主了榆樹9 一具付左兩和立契,畫指為信10 園主大女□□[10]。
契約因為是租佃契,粗看似乎沒有什麼不平等的地方不過在契約第8-9行的附加條件當中,我們看到園主呂玉必須將榆樹一具交付給左這應當是左憧憙在此次交易中,所提的附加條件如是這樣,則租金實際低於“錢(捌)文”透過以上三件契約以及其它契約我們大致能看到,左憧憙善於多方經營,擁有奴婢、田園,有數量可觀的銀錢可供放貸。
墓誌說左憧憙財豐齊景,必是誇張的手法不過,唐代前期的民間詩人王梵志有一首詩《富饒田舍兒》,最適宜描述左這樣的富裕農戶:富饒田舍兒,論情實好事廣種如屯田,宅舍青煙起槽上飼肥馬,仍更買奴婢牛羊共成群,滿圈養肫子。
窖內多埋穀,尋常願米貴里正追役來,坐著南廳裏[11]廣設好飲食,多酒勸遣醉追車即与車,須馬即与馬須錢便与錢,和市亦不避索麵驢馱送,續後更有雉官人應須物,當家皆具備縣官与恩澤,曹司一家事縱有重差科,有錢不怕你。
[12]根據王梵志詩記述可知,這些富裕的農戶擁有數目不少的田地和宅舍,財力雄厚家中馬槽飼養著肥馬,花費甚多,但仍然有錢購買奴婢家中牛羊成群,猪圈擠滿小猪窖藏不少穀物,富饒田舍兒平時內心最期待的事,就是米價上漲,以便奇貨可居。
正因為富饒田舍兒家財頗豐,所以即便面對里正催逼賦役,也毫不擔心里正被富饒田舍兒用好酒好肉招待,常常痛飲至醉里正需要馬,富饒田舍兒就給馬,需要車便給車,要錢遂給錢,和市也不需要東西躲避[13]如果需要麵粉,富饒田舍兒就親自用驢運送。
在麵粉後接著運送的還有雞官家需要的東西,富饒田舍兒家無所不有里正需要什麼,富饒田舍兒從不為難富饒田舍兒與官府合作和諧縣衙的官員便給予恩澤,縣里的各辦事部門與他熟絡,好似一家人縱使有沉重的苛捐雜稅,富饒田舍兒因為有錢也無所畏懼。
這裏的富饒田舍兒相當於富農、地主從詩歌看,富饒田舍兒因為富,在鄉間就可以無所不能在詩歌中,富饒田舍兒雖然面對五花八門的徭役,卻有財力應付有餘王梵志的這種描寫其實也透露出,鄉間的農戶不得不面臨著沉重的賦役差科,或出錢、或出物、或出力。
[14]眾所周知,在唐代前期,賦役按照丁中制徵收在丁中為本的前提下,還保留“戶等” 的意義就在於戶等是徵發雜徭的依據戶等根據人丁多寡、貧富程度來劃分農戶如果不是足夠富裕,也不是完全有能力負荷年復一年的賦役、不定期徵發的雜徭是唐朝百姓沉重的負擔。
換句話說,在唐代前期,富裕也並不是什麼好事情“富”意味著戶等比較高,要承擔大量的差科所謂:“差科取高戶,賦役千百般”[15]王梵志也曾創作《他家笑吾貧》一詩,通過窮人的口吻,指出窮富相對的好處:他家笑吾貧,吾貧極快樂。
無牛亦無馬,不愁賊抄掠你富戶役高,差科並用却吾無呼喚處,飽喫常展腳你富披錦袍,尋常被纏縛窮苦無煩惱,草衣隨體著[16]這首詩歌流露著窮人“自我慰藉的情緒”詩中的主人公說別人笑我貧窮,但我覺得貧窮也十分快樂。
家中無牛也無馬,不擔心盜賊抄掠你家雖富而戶等高,要承擔大量雜徭[17]因為窮,我戶等低,他們派發徭役也無處找到我,我吃飽後就能展展拳腳你富裕穿著錦袍,平常被漂亮的衣服束縛窮苦反而沒這樣的煩惱,草衣隨身穿著便行。
雖然我們不能清楚左憧憙的戶等,不過要以《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西州蒲昌縣定戶等案卷》為標準,左憧憙所擁有的奴婢、菜園、銀錢等財產,均是評定戶等依據[18]號稱“財豐齊景”的左憧憙不可能像王梵志筆下的貧兒躲過這些差科。
其實,左憧憙身充府兵也應該和他家的富裕情況相關《唐律疏議》卷一六“揀點衛士征人不平”條稱:“揀點之法,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19]這就是說在唐前期,除了雜徭的派發依照戶等之外,能被徵發成為衛士、征人的丁口按原則也出自富戶。
《舊唐書》卷七〇《戴胄傳》記“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說的就是這樣的情況 [20]左憧憙可能因為家財頗豐,被揀點為西州前庭府府兵唐長孺先生曾仔細統計過唐西州衛士戶等及戶內丁口,得出這樣的結論:“唐代律令要求儘先揀點富室強丁充當衛士,吐魯番文書反映高宗時期的衛士均點自七等戶以上,說明當時也儘可能按律令辦理。
”[21]根據唐先生統計的樣本以及左憧憙作為唐高宗時西州高昌縣白丁充當府兵事實,我們大致可以推斷左家的戶等也應在七等之上墓誌說左憧憙“純忠敦孝,禮數越常”這裏不清楚左憧憙家庭成員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左憧憙的墓葬中曾出土一幅樸拙的女性畫像,上面題有“妻合端身”。
[22]合端,即突厥語可端,指妻子,研究者曾懷疑這位女性就是他的妻子[23]左憧憙墓中保留的《唐瀵舍告死者左憧憙書為左憧憙家失銀錢事》透露出他有個弟弟叫瀵舍[24]據現存資料也無從得知他敦孝父母的實情,但我們知道檢點府兵“同戶之內,每三丁取一丁”,成為府兵後在出征的時候“若父兄子弟,不併遣之;若祖父母、父母老疾。
無兼丁,免征行及番上”,[25]左憧憙應當代表家庭被揀點為府兵,凡遇戰事則需遠征也許替父替弟從軍代役本身這點就是孝的表現读者们熟知的木蘭,正是在其“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的情況下,代父出征,贏得了孝的美名。
代父從軍的例子在沙州敦煌縣也存在《武周久視二年(公元七〇一年)沙州敦煌縣懸泉鄉上柱國康萬善牒為以男代赴役事》是為例證:

武周久視二年(公元七〇一年)沙州敦煌縣懸泉鄉上柱國康萬善牒為以男代赴役事 1 牒萬善今簡充馬軍,擬迎送使萬2 善為先帶患,瘦弱不勝驅使,又復 同3 (年)老,今有男處琮,少壯仕,又便弓4 馬,望將替處今隨牒過,請裁。
謹牒5 久視二二

(月)

(日)懸泉鄉上柱國康萬善牒6 付 司[26]文書指出沙州敦煌縣懸泉鄉上柱國康萬善於久視二年訴說自己因為患病,身體瘦弱,不堪驅使,又因為年老,所以上牒報告希望自己的兒子處琮代替自己被簡點為“馬軍”當然,也有與木蘭、康處琮相比不孝的例子。
在王梵志筆下,曾有一個忤逆子,自己逃役,迫使父親替代,終致母親負氣而死:父母是怨家,生一五逆子養大長成人,元來不得使身役不肯料,逃走背家裏阿耶替役身,阿娘氣病死腹中懷惡來,自生煞人子此是前生惡,故故來相值。
虫蛇來報恩,人子合如此前怨續後怨,何時逍祖唯?[27]左憧憙與忤逆子自然不同,他是在戶有兼丁的情況下被派出遠征的府兵按照唐代府兵衛士的徵發年齡,所謂“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28],左憧憙於公元637年年滿二十一,正式成為前庭府府兵衛士。
作為府兵,政府對他們的生計、訓練方式,有著詳細的規定《唐六典》卷二五“折充都尉條”:“凡兵馬在府,每歲季冬,折充都尉率五校之屬以教其軍陣戰斗之法”[29]像左憧憙這樣的衛士日常訓練有素,戰斗力較強他們平時農耕,在農閒季節參與軍事訓練,遇到戰爭,則隨時出征,[30]如是年復一年,直至年齡入老。
[31]前庭府衛士左憧憙麟德二年(665)的一次出征記錄就保存在他墓葬中的文書里二麟德二年出征麟德二年(665),突騎施聯合吐蕃、疏勒進攻于闐[32]針對三國的聯合軍事行動,唐王朝下發詔令,命西州都督崔知辯,將領曹繼叔等派遣府兵和征人,於是年閏三月組成西域道行軍,救援于闐。
這一年左憧憙年滿四十九,作為西州前庭府的一員衛士加入此行[33]府兵出征,軍資、衣裝、輕武器(弓箭、橫刀)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糧食,均須自備每一火十人還得共備供運輸的馬六疋(或用驢),即所謂“六馱馬”[34]木蘭出征時在“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便是府兵自備資裝的表現。
府兵在什麼情形下才能自備資裝呢?府兵衹有在兵農合一之後,纔有能力仰賴均田收穫,準備當兵的衣裝[35]不過,即便擁有均田,籌備這些出征物資,在當時也是府兵沉重的負擔平時府兵所有的資裝存在軍府,到用時,向軍府領用。
左憧憙充當府兵,自然也免不了購置馱馬,在《支用錢練帳》(詳後)中,我們看到左在行軍途中也曾為馬購買飼料不過,他家足夠富裕,置辦資裝,不至於破產敗家物資準備齊全,軍情緊急,府兵出征迫在眉睫读者对于府兵出征场景最熟悉的记忆,应当还是稍显离愁的《木兰诗》:。
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木蘭渡過黃河,北至黑山(當即今內蒙巴林右旗小罕山)詩歌把遙遠的征途,化作筆下的豪邁木蘭途徑萬里遠征,度過艱險的關山,快若飛翔。
北邊的寒氣中傳來刁斗之聲,冰冷的月光照在鐵甲上,充滿了孤寂的色彩左憧憙西域道行軍的目的地是弓月城,根據相關文書可知,他行走路綫應當是安西都護府——拔換城——河頭——史德城——胡乍城——軄城——弓月雖然沒有文字留下來反映左憧憙的行軍之苦,但他行走於塔克拉馬干沙漠邊緣,環境惡劣可以想象。
與木蘭詩雄渾、豪邁的感覺不同,王梵志詩則以出征士兵的口吻指出府兵出征的辛苦與面臨的死亡危險,甚至覺得當兵生不如死:你道生勝死,我道死勝生生即苦戰死,死即無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磧裏向前走,衣鉀困須擎。
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鐵缽淹乾飯,同火共分諍長頭饑欲死,肚似破窮坑遣兒我受苦,慈母不須生[36]《木蘭詩》中,木蘭通過十年征戰,纔踏上歸程,回來覲見天子,被策勳十二轉,可以獲得最高的勳官上柱國天子進一步問,木蘭有何要求?要不要留在京城做尚書郎?木蘭歸家心切,表示衹願還鄉,不願做官。
木蘭歸來,家人重逢詩歌用三排六句,精練地描述出木蘭父母、大姐、小弟的欣喜之情:“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木蘭出行數年,歷經百戰,卻能平安回家當然是幸運者。
但如要從寫實的角度來說,生離死別,朝不保夕纔應當是出征士兵的常態王梵志筆下另一位西征吐蕃的兵夫就沒木蘭這麼幸運兒大作兵夫,西征吐番賊行後渾家死,回來覔不得兒身面向南,死者頭向北父子相分擘,不及元不識[37
]父母生育某兒,準備衣食,含辛茹苦地將他養大某兒長大成丁,未及孝敬父母,卻不得不按照國家法令充當兵夫吐蕃入侵西域,某兒自當遠行禦敵出乎意料的是,他在外遠征時,全家親人發生意外,不幸死亡等他征戰歸來,面對的卻是父子生死異路。
他悲傷感歎,如果是像這樣父子生死相離,還不如原來就和家人不相識王梵志詩筆調通俗、簡單,卻將兵夫的無奈與哀愁表現得恰到好處某兒痛不欲生與木蘭幸福團聚形成鮮明對比王梵志的數首詩歌都表明軍府將士如若出征,便隨時徘徊在死亡的邊緣。
[38]正因為外出征戰九死一生,所以府兵在當時被視作天下“最惡”的官職:天下惡官職,不過是府兵四面有賊動,當日即須行有緣重相見,業薄即隔生逢賊被打煞,五品無人諍[39]在作者王梵志看來,天下最壞的官職,沒有什麼能比的上府兵。
四方如果有賊人進攻,當日就需要出征打仗出征途中,如果有緣還能相見,如果德業淺薄,則必定生死隔絕碰到賊人需要打打殺殺,性命朝不保夕,所以即便可因軍功獲得五品的勳官,也沒有人爭奪本來,在唐代前期,府兵外出征行有一個最大的誘惑就是可以而獲得勳官,因勳官可以得到勳田、賞賜。
在《舊唐書》卷八四《劉仁軌傳》可以看到,唐初征伐高麗的時候,有很多百姓自願充當征人 所謂“人人投募,爭欲西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40]人人爭相投募的原因是從軍有機會獲得巨額賞賜,贏取勳官。
即便府兵不幸身死王事,家族也會受到撫恤優待政府追贈官職給亡者,官爵可以回授“子弟”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回亡者官爵與其子弟[41]不過,在唐前期,循隋之舊,獲得勳官、軍功很難。
按照唐人書寫墓誌的慣例,生前獲得的官職一定要寫在誌中但左憧憙墓誌顯示出,他身當衛士多年從未獲得過任何官爵,連勳官也沒有其實錢財頗豐的家庭,最有機會逃避兵役通過賄賂官府,可以“東西藏避,並即得脫”[42]王梵志詩也說“縱有重差科,有錢不怕你”。
沒有錢打點官府的人,雖是老弱,被推著後背,也要勞形遠征[43]那麼,這里就有一個問題,號稱“財豐齊景”的左憧憙不僅沒有逃脫兵役墓誌反而說他“鴻源發於戎衛……意氣凌云,聲傳異域”,好像絲毫沒有敘述出他的從軍之苦,誌中文字似乎是說他的富裕與從軍有關。
左憧憙為什麼樂意充當一個被視作惡官職的府兵?有兩件被吐魯番文書整理者命名為《支用錢練帳》的文書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文書顯示出左憧憙從軍買賣、進行貿易的一些情形這反映出儘管軍事遠征危險重重,但左憧憙能從戰爭中得到實際的好處。
這也體現出普通士兵從軍最直接目的《神機制敵太白陰經》說:“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44]我們大膽推測,墓誌之所以說左“鴻源發於戎衛”,是因為從軍有利可圖

唐支用錢練帳一支用錢練帳一支用錢練帳二1 三將去五疋,校尉買去二疋,用買何堛馬練2 □軄城下用練一疋(糴)馬䜺,更錢八文亦用胡乍城,更用練一疋3 用錢拾文,憧麥用麥造糧據史德城用錢4 □文,校尉用四文,䜺。
用錢二文,買弦更練一疋,曺師邊用䜺5

渾用練一疋,麨來回河頭用一疋,曺願住處 買羊更用錢6 □□住內撥換城用練半疋,米買婢,闕練一疋,更用錢7 □□買宍(肉)更用一疋,買白氈用練半疋尾乳處買氈用錢三文8 □安西用錢三文,䜺更用錢一文,買草更用同(銅)錢貳拾二文䴰(一)。
9 蓿。更用同錢六文,

更用同錢十四文,10 錢一十八文,更用同錢11 䜺用 銀 錢 二 文 買一腳宍更 用錢廿一文買䴰12 練13 □錢作用14 □□正一文索用練一疋與作□用15 錢壹拾三文,更錢校 尉下銀錢六文,銅錢六十文。
16 安校尉下銀錢六文,銅錢卅一文韓校尉下,銀錢六,銅錢伍十文,趙師下17 銀錢十文,銅錢六十文,更銅錢廿十六文,(二)張師下,銀錢七文,銅錢 卅文注釋(一)䴰:據下件當是“麨”之誤(以下第一一行同),其上疑奪一“買”字。
(二)廿十六文:疑衍一“十”字1 二疋用買何塠2 疋,馬䜺更錢3 練馬䜺更用 錢十4 糧據史德城用錢四文,与5 索用錢二文,買弦更用練一疋,6 曹師邊用回來河7 頭用練一疋,曹願住處買羊□用 錢還買肉。
8 撥換城用練 半 疋,糴米。買婢,闕二文, 撥換9 願住處買肉。更用 練一疋買白□□用

10 用錢三文,作齋更到安西用錢三文,䜺11 用同(銅)錢廿二文,買麨用同錢六文買苜12 更用同錢八文,買四□苜蓿更13 用錢六文,買三束苜蓿更 用同14 文,買一腳更用銅錢□由於《支用帳》殘破不堪,其性質曾引起較大爭議。
有的學者從文中出現很多“校尉” 稱呼以及涉及物資多為軍資來看, 認為這似乎有可能是一份軍隊後勤機構的官方賬簿[45]有的學者認為這份賬簿出自左憧憙墓中, 而且原件和抄本各一份從同墓其他文書看, 左憧憙在軍中的身份也並不是掌管後勤賬目的官員, 所以把這件文書認為是私人帳簿應更為合理。
[46]通過《支用錢練帳》透露的眾多信息來說,顯然后者的意見更為妥當這兩件《支用錢練帳》雖然殘破,但卻透露出行軍路線、行軍生活等眾多信息《神機制敵太白陰經》云:“軍無輜重,則舉動皆闕士卒以軍中為家,至於錐刀,不可有缺。
”[47]府兵出征準備的輜重、資財,學者們一般用《新唐書·兵志》的一段史料來說明: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
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並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48]這段史料,應當區分同火、同隊、個人三方準備的不同輜重。
同火共備的是六馱馬,烏布幕以下至鐮合計十四種同隊共備的是火鑽至足絆共四種而個人自備的除食物麥飯,米之外,為弓矢至行藤共九種[49]陳仲安先生認為個人自備中,弓矢和胡祿當合為一事,為箭囊,加上其餘六項事共為七項,是為“隨身七事”。
[50]需要注意的是,除同火、同隊、個人共備財物外,每個士兵出征之時還準備一定的私財《李衛公兵法》:“諸兵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並衣資、弓箭、鞍辔、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己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押署。
營司抄取一本,立為文案”[51]谷霽光先生認為其中的服、被、資、物、弓箭、鞍轡、器仗等為隨身七事陳仲安不同意谷霽光先生的看法,認為這條軍令是指兵士入營時,營官應檢視登記屬于兵士個人所有的衣裝財物,由於每人所帶數量不同,故須一一檢查登記,以備下番出營時減去消耗退還本人;如果戰死,則需要同火幫忙,根據所注州、縣、府衛退還給家屬。
[52]《唐律疏議·雜律》引《軍防令》:“征行衛士以上身死,行軍具錄隨身資財及屍,付本府人將還”[53]這條軍防令也顯示出,征行衛士除共備財物外,在征行過程中,還攜帶一部分私有錢財,供出征使用《支用錢練帳一》第1行顯示出,當同行校尉買馬隨身帶練不足,便向左憧憙買練。
校尉為什麼要在旅途中買馬呢?根據日本《軍防令》的記載,府兵十人一火共備六馱馬,馬在差行日“若有死失,仍即立替”[54]校尉的馱馬在路途是丟失,病死?我們不得而知這裏有一種可能的推測,即校尉買馬是在補充因故缺失的六馱馬。
在唐代西州以西,購買大宗商品馬、奴婢之類,均需要用練唐代的馬亦分等級,《天寶二年(743) 交河郡市估案》曾區分幾種不同的馬:突厥敦馬壹疋 次上直大練貳拾疋、次十八疋、下十陸疋……草馬壹疋 次上直大練玖疋 次捌疋下 柒疋。
……[55]按照《新唐書·兵志》所載,每個府兵自備“麥飯九斗,米二斗”,藏於府庫,出征時按需發放根據《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可以知道每個士兵每日糧食的需求量:“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其大麥八分,小麥六分,蕎麥四分,大豆八分,小豆七分,宛豆七分,麻七分,黍七分,并依分折米。
”[56]按照《倉庫令》的記載,一個丁男每天的食量大約也是二升米,“諸給糧,皆承省符丁男一人,日給二升米……”[57]根據以上《神機制敵太白陰經》的開列推算,每人每天吃米二升,如果是其他糧食的話,每人每天需要大麥2.5升餘,小麥3.3升餘,大豆2.5升餘,小豆2.86升,豌豆2.86升,麻2.86升,黍2.86升。
也就是說每個士兵儲存在府庫的麥飯九斗,米二斗大約可供一個出征士兵吃四十天左右左憧憙麟德二年閏三月出征一直到是年八月二十五日還在歸途,沒有到達安西都護府如果超過四十天,每人儲備的口糧就明顯不足而且出征途中也不能衹吃糧食,還需要肉食、豆類補充營養。
士兵所使用的武器也可能出現損耗,需要隨時購買這樣一來,士兵必然攜帶多餘的財產出征以備不時之需按照《李衛公兵法》的記載,這些財產似乎需要統一登記,形成文案《支用錢練帳一》第6行顯示出左憧憙途徑撥換城(今阿克蘇)時,曾用“練半疋,(糴)米”。
《支用錢練帳二》第8行“撥換城用練半疋,糴米買婢,闕 ”根据《天寶二年(743) 交河郡市估案》的資料可以轉換按照唐朝的習慣取中估,大練一疋值銅錢四百六十文半疋練相當於二百三十文銅錢按照記載,麒德三年長安每斗米低至五文,半疋練可以買38.3多斗米。
38.3多斗米夠一個人一個人吃六月西域物價可能偏高,如果按照《交河郡市估案》來算,米麵行中估白麵一斗值三拾柒文 米麵行白麵壹㪷 上直錢三拾八文 次三拾柒文 下三拾陸文北庭面壹㪷 上直錢三拾伍文……[58]
二百三十文可以買中估的白麵六斗多,可供一人吃三十天六斗米重量約今天100斤,征途当中應該用馬馱行[59]除米之外,左憧憙一路還買麥造糧,買羊、買肉、買䜺(碾碎的豆子)補充營養《支用錢練帳一》第3行顯示出左憧憙“用錢拾文,憧麥。
用麥造糧據史德城”《支用錢練帳一》第5行記“用一疋,曺願住處買羊”《支用錢練帳二》第7行行“用練一疋,曹願住處買羊”第7行记“□□買宍(肉)”《支用錢練帳二》第7行“□用錢還買肉”《支用錢練帳一》第8行“□安西。
用錢三文,䜺”《支用錢練帳二》第10行“更到安西用錢三文,䜺”與人的食物消耗相比,馬更需要大量的食物餵養所以我們看到,左也用練購買大宗馬料《支用錢練帳一》第2行記 “□軄城下用練一疋(糴)馬䜺更錢八文,亦用胡乍城。
更用練一疋”根據《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可以知道馬每日的食物包括粟、盐、茭草:一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百,六個月一十八石計一軍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萬七千五百石,六個月二十二萬五千石馬鹽,一馬日支鹽三合,一月九升,六個月五斗四升。
一軍馬支鹽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個月六千七百五十石茭草,一馬一日支茭草二圍,一月六十圍,六個月三百六十圍計一軍馬六個月九十萬圍[60]如果粟作為主糧,馬每天要吃一斗按《天聖令·厩牧令》宋令規定,馬要吃豆與蒿,具體數量,詳下記載:。
諸繫飼,給乾者,象丁(一)頭,日給稾(十)五圍;馬一匹,供御及帶甲、遞鋪者,各日給稾八分,餘給七分,蜀[馬]給五分;(其歲時加減速之從(數)[四],並從本司宣勅下及諸畜立(豆)[五]、鹽、藥等,並准此……)。
諸繫飼,給豆、鹽、藥者,……馬一匹,俱(供)御及帶甲、遞鋪者,日給豆八升,餘給七升;蜀馬[日給]五升;驢(騾)一頭,日給豆四升、麩一升月給鹽六兩、藥一啗運物在(道)則(者)[五],日給鹽五勺;(道)[六]冬月啗藥,加白米四合。
驢一頭,[日]給豆三升、麩五合,月給鹽二兩、(日)藥一啗[61]如果是供皇帝及帶鎧甲、遞鋪的馬,每日給豆八升,蒿草八分普通馬給豆七升,蒿草七分豆的日給量少於《神機制敵太白陰經》規定的一升粟根據喂馬者的經驗,飼馬用豆,馬的奔跑能力、耐力會加強。
左憧憙在路途中不停地買馬䜺、草、苜蓿,應當是出於日常飼馬的需求[62]另外,最能引起人們關注的是,左憧憙在西域返程的途中,準備了三種貨幣銀錢、銅錢、還有練,備齊這三種貨幣,表明左憧憙在常年的西域生活中,已經熟悉那里的貿易狀況。
比如,左憧行進到安西,用錢三文,䜺更用錢一文,買草銀錢的價值較高,攜帶數量也需求較小《支用錢練帳一》第16-17行云:安校尉下,銀錢六文,銅錢卅一文韓校尉下,銀錢六,銅錢伍十文趙師下,銀錢十文,銅錢六十文,更銅錢廿十六文。
張師下,銀錢七文,銅錢 卅文師、佐常指工匠,但出現在軍隊裏,與校尉並列,讓人殊難理解陳國燦先生推論這里的師當作帥,指旅帥,所論有理[63]我們不知道,安校尉、韓校尉、趙師、曹師下的銀錢為什麼要羅列在這裏?是發生的借貸,還是校尉與左發生了買賣關係?不過,唐代軍令嚴格限制軍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強取兵士的錢財。
“官典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64]《支用錢練帳一》第4行中曾有“校尉用四文……更練一疋,曺師邊用”好像表明有校尉或者姓曹的旅帥委託左憧憙保管錢財,一路上購買物資安校尉、趙師下的銀錢是委託左來管理,在整個征途結束後的結餘?。
左憧憙在一路上所購買的部分物品,和《新唐書·兵志》所列府兵資裝對應無遺:買馬火備六馱馬麥,米麥飯九斗,米二斗買弦人具弓一,矢三十買白氈用練半疋尾乳處買氈氊帽、氈裝左憧憙作為府兵在返程的途中,除了購買糧食、資裝以供日常生活外,他還在撥換城買婢,購買的時候缺練一疋。
在這樣的情況下,是要向他人借貸?買練?還是有其他什麼辦法?這裏也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這時候人口販賣在西域地區,也是重要的獲利之源有專門的“口馬行”經營這樣的生意[65]不過,如果熟知唐代軍事法令,就會明白左憧憙買婢這件事的“特殊性”。
杜甫《新婚別》詩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66]《通典》引《衛公兵法》云:“奸人妻女,及將女婦入營,斬之”[67]李筌《神機制敵太白陰經》云:“侵欺百姓,奸居人子女,及將婦人入營者斬,恐傷人,軍中慎女子氣。
”[68]日本《令義解·軍防令》云:“凡征行者,皆不得將婦女自隨”令後解釋強調說:“謂家女及婢,亦不可得隨也”[69]看到這樣的軍令,自然也會產生一個問題,既然軍令嚴格禁止,違規的代價是殺頭,那麼,左為何在軍營中買一個女婢隨身攜帶?這裏很自然的聯想便是左或許與自己府內的長官有特殊的私交,得到了某種默許或通融。
除《支用錢練帳》外,相關契約也顯示出左在凱旋途中從事商業活動麟德二年西域道的行軍,除了有像左憧憙這樣的府兵之外,還有臨時徵募的兵員 “征人”所謂“征人” ,“謂非衛士, 臨時募行者”[70]在歸程中,西域道征人趙醜胡向同行的左憧憙借貸三疋帛練,所形成的借貸契約《唐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趙醜胡貸練契》錄如下:。
1 麟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西域道征人趙醜2 胡於同行人左憧憙邊貸取帛練3 叁疋其練回還到西州拾日內,還4 練使了到過其月不還,月別依5 鄉法酬生利延引不還,聽拽家財6 雜物平為本練直若身東西不在,7 一仰妻兒還償本練。
其練到安西8 得賜物,只還練兩疋;若不得賜,始9 還練三疋兩和立契,獲指為騐10 練主左11 貸練人趙醜胡12 保人白禿子13 知見人張軌端14 知見人竹禿子[71]這個契約也有不少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方幾乎所有研究這件吐魯番文書的人都看出問題所在。
此前左憧憙簽訂的借貸契約中都是高利貸,要標明月息:月別生利錢壹文然而在這件契約中,左憧憙卻一反常態,竟然沒有要征人趙醜胡的利息,而是相約回到西州十天之內歸還本練三疋如果在西州發生欠錢不還的情形,纔“聽拽家財雜物平為本練直”。
如果自身逃跑,則需妻兒償還“本練”如果到了安西都護府,得到賞賜之練,衹需歸還兩疋問題是趙借練三疋,除不收利息外,為何到安西都護府得賜之後,還可以少還一疋?關於如何解釋這個問題,學者們也出現了較大分歧其中,有些學者贊成“同鄉、同行優待說”。
唐耕耦先生認為, 在西州借練三疋, 到安西衹還兩疋, 可能是因為左憧憙作為征人, 在安西需要帛練使用, 而從西州到安西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少還一疋是充作運費左憧憙和同行士兵參與軍事行動, 在生死未卜的情況下,為了求得同行士兵的照顧, 就以無息貸款來買取友情。
[72]對於這個問題,筆者曾請教朱雷先生朱先生似乎也同意唐耕耦先生的看法朱雷先生認為“同行人”三字,蘊含著解開謎題的綫索他認為左與趙為同行人,這里的行並不是行走的行,而是行伍的行在朱雷先生看來,正因為二人是同行的火伴,行軍路途艱苦難耐,需要相互照顧,所以左憧憙在利息上給與趙醜胡特殊照顧。
錢伯泉先生也大概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如果勝利返回安西, 得到朝廷獎勵和賞賜的物品, 則趙醜胡衹還練兩疋, 其中一疋由債主左憧熹作為獎勵而免除了 如果趙醜胡不是左憧熹屬下的同鄉士兵 , 他決不會在借契中如此許願。
”[73]不過,在我看來,“同鄉、同行優待說”可能多少是理想化的看法,同行的軍人未必衹存溫情《通典》引《李衛公兵法·雜教令》云:“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恃己力強,欺傲火人,全無長幼,兼笞撻懦弱,減削糧食、衣資,并軍器、火具恣意令擎,勞逸不等。
”[74]軍令如此強調,其實證明在軍隊中以暴制弱,同火間相互欺淩的情形也時有發生按照王梵志詩的描述,如果征行的士兵因為饑餓,發生“鐵缽淹乾飯,同火共分諍”的事情或是常態 除征人趙醜胡外,左憧憙給府兵張海歡所貸銀錢也是免息。
這反映在《唐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張海歡白懷洛貸銀錢契》中在前往西州的道路上,張海歡與白懷洛向左借貸四十捌文銀錢,形成一個契約:

唐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張海歡、白懷洛貸銀錢契1 麟德二年十一月廿四日,前庭府衛士張海歡於左憧2 憙邊貸取銀錢肆拾捌文,限至西州十日内還本3 錢使了如違限不償錢,月別拾錢後生利錢壹4 文入左若延引注託不還錢,任左牽掣張家資。
5 雜物、口分田、桃(萄)用充錢直取若張身東西沒洛(落)者,一6 仰妻兒及收後保人替償兩和立契,畫指為信7 同日,白懷洛貸取銀錢貳拾肆文,還日,別部依8 上券同 錢主 左9 貸錢人張海歡10 貸錢人白懷洛。
11 保人張歡相12 保人張歡德海歡母替男酬練,若不上,依月生利大女李臺明 保人海歡妻郭如連13 保人陰歡德[75]麟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左憧憙仍然在歸途中,他們的最終目的地是西州(今吐魯番)與左同行的不僅有征人趙醜胡,還有同處前庭折衝府的衛士張海歡、白懷洛。
簡單來看,左憧憙在契約中依然“優待”同行的火伴雙方約定到達西州之日,衹需要還本就可以,如果錯過還錢日期,找各種理由推脫不還,左可以任意拿張海歡中的家資雜物、口分田、葡萄園抵債這里讓我們意外的是,唐代法律嚴禁交易的口分田,也被當作抵債的資產。
口分田被用來交易,還反映在吐魯番文書《唐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鄭海石舉銀錢契》中[76] 得輕還重,逐利輕義是民間借貸的一般原則,王梵志《得他一束絹》詩云:“得他一束絹,還他一束羅計時應大重,直為年歲多。
”《貸人五㪷米》云:“貸人五斗㪷米,送還一碩粟筭時應有餘,剩者充臼直” [77]陳國燦先生則由商人逐利本性的角度,從蛛絲馬跡當中,做了另外一種推測他說:“出貸者都是為了取利生息, 即為了剝削”[78]《張海歡白懷洛貸銀錢契》中所借銀錢數為四十八文、二十四文, 與通常借錢多取整數不符, 所以陳先生懷疑其實際應為貸取練帛的估價。
這樣,在償還時就可套取銀、練之間的差價因此,這一借貸文書表面上不需支付利息,實則並非無息借貸最終前庭府衛士張海歡也可能無力償還所借之錢,因為在契約末尾看到,張海歡的母親大女李臺明被要求替子償還練在這里,我們傾向陳國燦先生的觀點。
左憧憙在放貸之時,可能預設借貸者無力償還一旦償還失期,左憧憙經常攫取別人的不動產(田園 、口分田等 ),無息貸款談不上什麼同火的溫情唐代西州的民間借貸中,經常有人因無力償還物資,被一紙訟狀告向官府不過,也有學者對陳國燦先生的解釋提出質疑:“無息借貸文書肯定是存在的, 即使陳先生文中的觀點是正確的, 那也衹能對某一件文書進行解釋, 而同墓所出性質幾乎一樣的《唐麟德二年(665年)趙醜胡貸練契》, 陳先生文中就沒有給出解釋。
”[79]至於《唐麟德二年(665年)趙醜胡貸練契》中為什麼趙醜胡借練三疋免息之外,到安西都護府領到兵賜之後,還可以少還一疋?我想,這里唯一的解釋就是:之所以強調安西兵賜之練,可能是因為兵賜之練質量較好。
在《交河郡物價表》中,我們看到同樣是練,但確實有品種、等級的差異[80]安西的白練常來自中原,“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當時最好的絲織品都產自河南、河北[81] 三屈身卑己,立身修名?麟德二年的西域道行軍之後,直至咸亨元年,西域再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戰斗。
由此可見,此次行軍達到了戰略目的[82]可以說以左憧憙為代表的府兵、征人有力地抵禦了吐蕃的入侵墓誌說他 “意氣凌云,聲傳異域”,頗有昂揚的氣息,可能說的就是這次勝利的遠征在此後數年間,西域相對安定的環境大概也是左憧憙再沒有出征的原因。
左憧憙回到西州高昌縣崇化鄉後,依然從事放貸的營生,巧取豪奪數目眾多的同墓出土契約,透露著他的“致富經”契約顯示出一個叫張善憙的人和他往來最為頻繁乾封三年(668)三月三日,武城鄉人張善憙大概因為家庭遇到了困難,向左憧憙借錢渡急。
張善憙為了借貸順利,一塊喊來自己的女兒張如資、朋友高隆歡作為擔保人除此之外,還有見證人(知見)張軌端他們按照慣例在紙上畫了指節,與今天的按手印頗為相類交易過程形成一張契約,一直被左憧憙帶入墓葬當中內容如下:。
1 乾封三年三月三日,武城鄉張善憙於2 崇化鄉左憧憙邊舉取銀錢貳拾文,3 月別生利銀錢貳文到月滿,張即須4 送利到左須錢之日,張並須本利酬還5 若延引不還,聽左拽取張家財雜物平為6 本錢直身東西不在,一仰妻兒保人上錢使。
7 了若延引不與左錢者,將中渠菜園半畝,8 與作錢質,要須得好菜處兩和立契,9 獲指為騐左共折生錢,日別與左菜伍尺園,到菜幹日10 錢主 左11 舉錢人 張善憙12 保人 女如資13 保人 高隆歡14 知見人 張軌端[83]
根據契約可知,張善憙借左憧憙銀錢二十文,每月利息為二文,按月結息每月月滿的時候,張善憙必須把利息先償還給債主左憧憙等左憧憙需要錢的時候,張善憙必須將本金利息償還如果拖延不還,左憧憙可以拿張善憙家里的任何財產抵償債務。
假如找不到張善憙,他的女兒和擔保人要替他償還唐代“雜令”云:“如負債者逃,保人代償”[84]王梵志詩《無親莫充保》云:“無親莫充保,無事莫作媒雖失鄉人意,終身無害災”[85]由此可見,一旦借貸者無力償還,保人有不小經濟風險,所以在鄉間認為親人充保更為妥當。
契約7-8行“若延引不與左錢者,將中渠菜園半畝,與作錢質”,即指如果張過期不還,左就要將張的半畝菜園所有權拿過去除此之外,左憧憙的利息錢還可以用菜園所產菜來償還,但張必須每天送菜與左,一直到菜園沒法種菜的季節。
兩年之後,張善憙家庭似乎困難依舊,否則他不會繼續向左憧憙借錢四十文借錢內容反映在《唐總章三年(公元六七〇年)張善憙舉錢契》,契約內容如下:1 總章三年二[86]月十三日,武城鄉張善憙2 於左憧憙邊舉取銀錢肆拾文,。
3 每月生利錢肆文若左須錢之日,4 張即子本具還前卻不還,任掣家5 資平為錢直身東西不在,仰收後代6 還兩和立契,獲指為記7 錢主8 貸錢人張善憙9 保人男君洛10 保人女如資11 知見人高隆歡12 知見人王父師
13 知見人曹感[87]“銀錢肆拾文,每月生利錢肆文”,利息依然遠遠超過了唐王朝規定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為了順利借貸,張善憙應當是答應了左憧憙提出的附加條件,將自己在張渠的一塊田園租給左憧憙:1 總章三年二月十三日,左憧憙於張善。
2 憙邊夏取張渠菜園壹所,在白赤舉3 北分牆其園叁年中與夏價大麥拾4 陸(斛);秋拾陸更肆年,与銀錢叁拾文5 若到佃時不得者,壹罰貳入左祖(租)殊(輸)6 伯(佰)役,仰園主;渠破水讁,仰佃人當為7 人無信,故立私契為騐。
8 錢主 左9 園主 張善憙10 保人 男君洛11 保人 女如資12 知見人 王父師13 知見人 曹感[88]韓森敏銳地指出租佃田地的人、放高利貸者左憧憙,顯然比這塊田地的主人要富有得多[89]那麼,左為什麼要租佃呢?顯然是有利可圖。
這個契約也有蹊蹺之處,簽定時間在二月十三日春季,但左卻說“夏取”為什要夏天才取菜園呢?道理可能很簡單,三月、四月是田園的青苗期,離收穫尚遠,左不想白白付出耕作之功另外,在契約簽訂時,左沒有支付任何租金,而是將租金分解為四年支付,“三年中與夏價大麥拾陸(斛);秋拾陸。
更肆年,與銀錢三拾文”左沒有說具體租佃時間,也就是不管張善憙耕種與否,樂意與否,進入夏季左對於張渠菜園隨時可取如果張沒有按時交出田園,反而要將租金雙倍返還給左憧憙無論是舉錢契還是租佃契,我們似乎看到左憧憙最關心的是張家的田地。
因此有學者推測,左憧憙正是在契約中暗設玄機,一旦借貸者無力償還,左自然會攫取別人賴以生計的土地左憧憙一貫精明,還體現其它交易中兩年前,在總章元年(668年)六月三日,左憧憙向順義鄉人張潘塠買草,形成以下契約:。
1 總章元年六月三日,崇化鄉人左憧憙交用銀2 錢肆拾,順義鄉張潘塠邊取草玖拾如到3 高昌之日不得草玖者,還銀錢陸拾文4 如身東西不到高昌者,仰收後者別還若5 草好惡之中,任為左意如身東西不6 在者一仰妻兒及保人知當。
兩和7 立契,獲指為信如草□高昌□8 錢主左9 取草人張潘塠10 保人竹阿闍利11 保人樊曾□12 同伴人和廣護[90]上述契約的內容多少顯得有些苛刻,長距離運輸,卻不允許草料損耗一旦發生損耗,即要求順義鄉張潘塠賠償銀錢六十文。
左憧憙購買如此多的草料,用途是什麼呢?錢伯泉說這麼多草足夠他家的牛羊過冬[91]韓森認為這些草很可能是為他的羊群和駱駝買的[92]在沒有其它證據的情況下,兩種關於草料用途的推測都很合理從王梵志詩看,鄉間農戶富裕的一項指標即是 “牛羊共成群,滿圈養肫子”。
以上我們剖析的四個契約,都有極度不平等的地方所以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巧取豪奪的人能在鄉間有好的名聲墓誌說他“屈身卑己,立行修名”,讓人頗懷疑這是墓誌書寫者的諛詞王梵志詩說窮人“無牛亦無馬,不愁賊抄掠”但像左憧憙這樣銀錢充盈,奴婢成群,牲畜滿圈的富饒田舍兒,自然免不了被賊人惦記。
一件殘破的文書曾顯示乾封二年臘月十一日左憧憙家發生一起盜竊案左家丟失銀錢五百文1 乾封二年臈(臘)月十一日,左憧憙家內失銀錢伍伯2 文,盜(道)瀵舍盜錢其瀵舍不得兄子錢,家里3 大小曹主及奴是等及鎧相有人盜錢者,兄子。
4 好驗校分明嗦(索)取,里鎧有人取者,放令5 瀵舍知見其瀵舍好兄子邊受之往(枉)6 罪瀵舍未服,語兄分明驗校,瀵舍心下7 得清淨意古(故)若瀵舍不取之錢,家里曹主及8 大小奴婢及鎧人放,瀵舍眼見,即於死者咸亨四。
9 年四月廿九日神遇已後,見多放,即須知錢10 之往,要須大小得死,瀵舍即知[93]本件文書並未講左家丟失銀錢過程,衹是主人公“瀵舍”分辨自己及家人奴婢等並未盜過銀錢“瀵舍”,人名,“瀵”應即“糞”之借字,敦煌文書中多見“張糞定”“穆糞子”“陳糞糞”及“氾糞堆”“王糞堆”“李糞堆”“程糞堆”“索糞堆”“段糞堆”等一類賤名。
“瀵舍”,從行文看,似亦應姓“左”,為“左憧憙”之弟,故屢稱“兄”如何本件是告訴“左憧憙”,自己及家人(大小曹主及奴是等及鎧相)等均未拿過“兄子”即“左憧憙”之子的伍百銀錢“曹主”,此處應指有錢財的主人。
王梵志《天下浮逃人》詩:“強處出頭來,不須曹主喚” [94]曹主經常與奴婢相對《敦煌變文集·目連救母變文》:“弟子於師長之床,奴婢于曹主之床” 因此,這里的曹主應當指瀵舍的家人“鎧”“里鎧”“鎧人”之“鎧”,應是借字,但不解何義。
我想可能是家內衛士之類瀵舍希望左憧憙的兒子拿出證據讓自己看到但左憧憙之子好像並沒有拿出什麼可靠的證據瀵舍說自己在侄兒那裏受了冤罪,希望左憧憙仔細查驗,還自己清白,使得自己內心獲得平靜[95]四月廿九日不是瀵舍陳情的日子,而是左憧憙死前一個很特殊的日子,在這一天,不但左憧憙“神遇”,即發生精神感知,而且同墓的《左憧憙生前功德及隨身錢物疏》云:“咸亨四年四月廿九日付曹主左×校收取錢財及練、伍穀、麥、粟...”,聯繫文書前面內容,這些東西應該都是他的陪葬品。
另外,左憧憙家失銀錢之事在乾封二年,何以八年之後舊事重提?可以推斷,此事應該不是瀵舍先提的,因為文書中說他“受之枉罪”,他認為自己是被哥哥左憧憙冤枉的,因此不大可能在八年後,尤其是在他哥病中舊事重提重提舊事的衹可能是一個人,那就是左憧憙。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場景:咸亨四年四月廿九日,得了重病的左憧憙突然感覺身體好一些了,但他深深知道自己時日不多,於是趕忙收納、核對財產,安排自己的隨葬品和其他後事在這時他又想起了八年前丟失銀錢五百文之事,這可能是精明了一輩子的左憧憙晚年的一大心事,他一直懷疑自己的弟弟瀵舍或者他的家人、奴婢拿了這筆錢,遂又叫瀵舍前來對質。
兄弟俩究竟談得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還是不了了之文書云即於“死者咸亨四年四月廿九日神遇已後,見多放,即須知錢之往”,“見多放”不知何意,這段話大概可以理解為,左憧憙可以通過精神感知這筆錢到底去哪了,被誰偷了。
如果知道了,就讓那人去死這樣瀵舍就可以知道盗者为谁,洗刷自己的冤情如何理解這種民間家庭因財產發生的糾紛?我們想到依然是王梵志所寫的兩首詩王梵志詩有《兄弟須和順》:“兄弟須和順,叔侄莫輕欺財物同箱櫃,房中莫畜私。
”[96]不過,在民間也經常因為第二代的出生,兄弟分家、禍起蕭牆的事情《兄弟義居活》:兄弟義居活,,一種有男女兒小教讀書,女小教針補兒大与娶妻,女大須嫁去當房作私產,共語覓嗔處好貪競盛喫,無心奉父母外姓能蛆妒,啾唧由女婦。
一日三場鬬,自分不由父[97]四躲過三惡道:左憧憙的死亡與信仰在《支用錢練帳》中曾出現“用錢三文,作齋”在凱旋途中作齋似有祈求平安之意根據《唐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左憧憙生前功德及隨身錢物疏》可進一步印證左憧憙的佛教信仰:。
1 憧憙身在之日告佛2 憧憙身在之日,十年已前造壹佛、貳陪(菩)3

(薩)。逕三年,說汙蘭貪逕(經)。左郎身自□4 伍佰僧齋[98]銀錢用。左郎隨身去日,將5 白銀錢叁

,白練壹萬段,清科(稞)、□麥、粟、

6 等伍萬石。婢阿迦、婢□香、婢多不脛、婢解、奴

7 德、婢尾香。咸亨四年四月廿九日付曹主左□8 校收取錢財及練、伍穀、麥、粟等

(斛)收9 領取用鎧(?)有於人,不得拽取付主左10 憧憙收領[99]文書1-2行表明左的信仰由來已久,十年以前曾造一佛二菩薩,還說《盂蘭盆經》三年,這是左憧憙的生前福德可能與這些功德關係到死後世界的生活。
王梵志詩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生前奉佛造像的行為《說錢心即喜》一詩說“說錢心即喜,見死元不愁廣貪財色樂,時時度日休平生不造福,死被業道收但看三惡處,大有我般流”[100]如果有錢人生前不造福業,不攢功德,死後有沉淪三惡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的可能。
如果一旦墮入三惡道,將是一個充滿酷刑、苦厄的世界:沉淪三惡道,負特愚癡鬼荒忙身卒死,即屬伺命使反縛棒駈走,先渡奈何水倒拽至廳前,枷棒遍身起死經一七日,刑名受罪鬼牛頭鐵叉扠,獄卒把刀掇碓擣磑磨身,覆生還覆死。
[101]這里稍微需要辨析的是文書第3-4行,該行內容原整理者將此“斋”字釋為“表衣”,但不可解,經仔細辨識“表衣”應合為一字,當作齋的異體字

表明他曾捐出五百僧齋銀錢南北朝以後民間有人死後累七修齋,興辦法事,以求未來冥世之福《北史》卷八十《胡國珍傳》:“詔自始薨至七七日,皆為設千僧齋”[102]王梵志詩說“有意造一佛,為設百人齋”[103]左伍佰僧齋應該就是設七七齋,以求渡過地獄苦難。
不過,五百僧齋的規模顯然是超過了唐王朝限定的標準,非貧家可為《唐六典》祠部對於官私設齋有嚴格的規定,其中就指出私家設齋不得超過四十九人[104]五百僧齋的規模再次展現出左憧憙的巨大財富左不惜奉獻錢財,舉辦佛教齋儀,目的還是為了避免死後沉淪三惡道。
按照王梵志的詩歌描述,一旦沉淪三惡道,人將飽受地獄之苦,家財、奴婢、美食都不能享用:沉淪三惡道,家內無人知有衣不能著,有馬不能騎有奴不能使,有婢不相隨有食不能喫,向前恒受飢冥冥地獄苦,難見出頭時依巡次弟去,卻活知有誰?[105]。
不過,經過造像、寫經、設齋,左憧憙似乎認為自己會躲過“三惡道”,因為我們在文書的第4-9行看到左攜帶了不少奴婢、錢財、食品,企圖在地下世界享用當然,學者們大都認為這些奴婢應當是紙張做的偶人結語:制度與個體。
左憧憙歷經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是西州高昌縣祟化鄉人他幼年、青年的事情我們不大清楚從他墓葬中透露出的多種信息來看,人們的直觀感受是他確實比較富有墓中出土的多種契約表明,他日常生活中擅長高利貸經營高利貸的月息按“鄉法生利”,達百分之十左右,明顯超出了唐政府的法律規定。
但正是通過這樣的法外經營使得他生活富足無憂富裕程度在唐王朝的法律中,用“戶等”這樣的專有名詞來標識富有代表著他可以過衣食無憂的生活,但同時戶等高也意味著他家要承擔大量徭役以及兵役我們不清楚左憧憙家的具體戶等,但從他被揀點為前庭府的府兵這點來看,應當是遵循了唐王朝揀點府兵“戶高丁多”的制度原則。
按照法律規定,作為前庭府普通衛士,他免不了外出征戰,好在此時吐蕃衹是在西域進行小規模的騷擾,戰爭規模不大,這大大降低了軍事遠征的風險他最終凱旋而歸,順利返鄉返鄉過程中的一個帳本和兩件契約,反映出他很有經營頭腦,給同行士兵放貸、進行人口貿易,在出征的途中依然不放棄營利。
墓誌說他“意氣陵云,聲傳異域”,似乎是要贊揚他的軍事功績但如果從稍後的西域局勢來看,這顯然是他生得其時,沒有遇上吐蕃大規模入侵西域的戰爭在他去世前三年的咸亨元年,吐蕃一舉攻陷了安西四鎮,戰爭規模則更大更慘烈,出征士兵自然九死一生。
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是一名幸運兒左憧憙身當府兵多年,但墓誌顯示出他從未獲得過任何官爵,連一個隊長都不是這當然也表明唐前期獲得勳官等功勳的難度雖然如此,但這並不妨礙他過富裕的生活回鄉之後他依然從事高利貸的經營,從縣鄉借貸人身上無情勒索,巧取豪奪。
[106]墓誌說他 “立行修名”,但諸種不平等的契約讓我們看到唯利是圖才是他生活的方式我們甚至可以說,左憧憙獲得了大量不義之財金钱也常常带来烦恼乾封二年他家中丟失五百銀錢,他一度懷疑弟弟就是盜賊兄弟因錢義斷大概也是他臨死前都耿耿於懷的事情。
但日常生活中,有一項支出,他卻从不吝啬相關文書透露出,他信仰佛教宗教的教義要求獲得錢財,需寫經造像,捐助功德,抵消罪業否則死後有沉淪三惡道的危險因此他不惜斥鉅資造一佛二菩薩、說盂蘭盆經三年,積攢福德儘管唐王朝的法律規定,私家設齋不得超過四十九人,但他曾一次性付出五百僧齋的銀錢,無視法律的規定,為自己祈福。
這些宗教行為的目的衹有一個,就是為了避免沉淪到惡鬼、畜生、地獄三道,受盡酷刑折磨而躲過三惡道,他將繼續享有美食、奴婢等財富是什麼能驅使左捨棄自己苦心經營的錢財?答案很明顯,就是信仰通過對左憧憙這樣一個個案研究,我們不求得到撼動整個府兵制度研究的結論,我們衹是想通過對相關材料的剖析,復原一個唐前期衛士的生活片段,給稍顯枯燥的制度史的骨架增加新的血肉。
我們試圖瞭解一下在體制中一個個體對制度的遵循、背叛、掙扎與自我調適的諸多面向有關左憧憙的一生經歷,我們目前就知道以上這麼多信息但最近朱雷先生見告,左憧憙墓出土的文書還有一些,正在整理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些文书片段认识统一制度下的不同个体。
附記:本文在寫作修改的時候,王素、劉安志、侯旭东、陳麗萍、王安泰、孫齊、羅亮、武绍卫、馮濤、李兆宇等諸位師友多有提示指正,在此專致謝意!注 釋[1] 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二《天下惡官職》,158頁[2]有關中古學者關於府兵制的研究,可以參考孫繼民《政治卷》第三章《兵制》,收入胡載、張弓、李斌城、葛承雍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17-136頁 。
孟彥弘《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地區唐代兵制研究概觀》,《中國史學》第11卷,2001年10月有關日本學者的府兵制研究,可參見氣賀澤保規《《府兵制の研究》,同朋舍,1999年,3-66頁[3] 如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西域史事二題》,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集, 1990年, 345 —351頁。
陳國燦:《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軍的救于阗之役——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四號墓部分文書的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十二期,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27-35頁[4] 參見張蔭才《吐魯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幾件唐代文書》,《文物》1973年第10期。
陳國燦:《唐代的民間借貸——吐魯番敦煌等地所出的唐代借貸契券初探》,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83年后收入氏著《唐代的經濟社會》第六章《唐代的民間借貸》,文津出版社,1999年卢开万《唐前期西州地区高利贷盤剥下均田百姓的分化》,《敦煌学辑刊》 1984年 第2期 。
唐耕耦《唐五代時期的高利貸——— 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文書初探》, 《敦煌學輯刊》1986 年第1期錢伯泉《從 考察唐初西域的政治經濟狀況》,《新疆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美]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魯西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趙志超《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士兵借貸問題研究》,《西域研究》 2009年第 2期等等[5] 墓誌錄文,參見張蔭才《吐魯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幾件唐代文書》,《文物》1973年第10期,73頁[6]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 209頁。
[7] 竇儀等詳定《宋刑統校證》卷二六引“雜令”:“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官不為理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壹倍”岳純之校證,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350頁[8] 《唐會要》卷八八《雜錄》引開元十六年詔令:“自今以後,天下負舉,職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919頁)“宜”自然是建議之語但在開元二十五年杂令裡,我們看到唐王朝的建議是:“諸公私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官不為理,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同參陳國燦《唐代的經濟社會》第六章《唐代的民間借貸》第二节《生息借贷中的剥削率》,文津出版社,1999年,172-211頁。
[9]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12頁[10]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10頁[11] 里正与唐代赋役的问题,研究前史丰富综合诸家学说的研究,可以参考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家与集落》第八章《唐户令乡里·坊村▪邻保关系条文の复原をめぐつて》;第九章《唐代の乡里制和村制》,汲古书院,1996年,第375-495页。
[12] 參考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五,項楚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553頁[13] 唐代和糴米也是和市的一種,吐魯番文書顯示出,和糴也按照百姓戶等來派發詳參盧開萬《唐代和糴制度新探》,《武漢大學學報》 1982年 第6期。
[14] 張澤咸先生指出:“差科的內涵離不開稅、役兩個方面”詳參氏著《唐五代賦役史草》,中華書局,1986年,356頁凍國棟同意這種意見,並進一步論證詳參氏著《管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輯,1994年。
後收入《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291-292页[15] 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二《當鄉何物貴》,109頁[16] 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一, 25頁[17] “你富戶役高,差科並用卻”,依然透露著唐代賦役法規。
唐代雜徭、差科派發依照戶等,原則是戶高丁多詳參《唐律疏議箋解》卷一三《戶婚律》”差科賦役違法”條,卷十六《擅興律》“丁夫差遣不平條”,第1001頁,1224頁[18]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311-312頁。
[19] 《唐律疏議箋解》卷一六《擅興律》“揀點衛士征人不平”,中華書局,1173頁[20] 《舊唐書》卷七〇《戴胄傳》,中華書局,2534頁[21] 參看唐長孺: 《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後收入氏著《山居存稿三編》,中華書局,2011年,第250頁[22] 參考李征《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發掘簡報(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23] 韓森推論說:“放高利貸者左憧憙與一位突厥婦女結婚了嗎?或者他本人就是突厥人。
”[美]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魯西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35頁[24]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29頁[25] 《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郎中員外郎條”,中華書局,1992年,156頁。
[26]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410頁[27] 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五《父母是怨家》,592頁[28] 《唐會要》卷七二《府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538頁[29] 《唐六典》卷二五“折衝都尉”,644頁。
[30] 有關府兵征鎮戍的問題,可參看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西州府兵》,《山居存稿三編》, 260-292頁[31] 有關府兵的出征制度,可以參看孫繼民《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府兵的征行制度》,收入《敦煌吐魯番文書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21-130頁。
[32] 最新的研究,可參考劉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軍政體制研究》,中西書局,2016年,162-166頁[33] 關於此次戰役,可參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西域史事二題》,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集, 1990年, 345 —351頁。
陳國燦《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軍的救于阗之役——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四號墓部分文書的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2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27-35頁[34] 關於府兵資裝自備及自備馱馬的問題,可以參考孫繼民:《吐魯番文書所見唐代府兵裝備》,《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
陳仲安:《唐府兵隨身七事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張國剛:《所謂府兵“隨身七事”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文津出版社,1983年孟憲實:《論唐代府兵制下的馱馬之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6卷 ,2016 年, 155—179 頁。
[35]從木蘭獲得軍勳十二轉來看,她應當是一個唐前期女扮男裝的府兵無疑(參考唐長孺《木蘭詩補證》,《江漢論壇》1986年第6期後收入氏著《山居叢稿續編》(《唐長孺文集》八卷本),中華書局,2011年,112-121頁。
)[36] 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五《你道生勝死》,533頁[37] 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五《父母生兒身》,502頁[38] 參見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五《相將歸去來》,第536頁[39] 王梵志《王梵志詩校注》卷二《天下惡官職》,158頁。
[40]《舊唐書》卷八四《劉仁軌傳》,中華書局,1975年,2793頁[41]《舊唐書》卷八四《劉仁軌傳》,2793頁[42]《舊唐書》卷八四《劉仁軌傳》,2793頁[43]《舊唐書》卷八四《劉仁軌傳》,2793頁。
[44](唐)李筌著《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五《軍資篇第六十》,盛冬鈴譯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2-63頁[45] 陳國燦《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軍的救于阗之役——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四號墓部分文書的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2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30頁。
[46] 趙志超《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士兵借貸問題研究》,《西域研究》 2009年第 2期,49頁[47]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四《軍裝篇第四十二》,49頁[48]《新唐書》卷五〇《兵志》,中華書局,1975年,1325頁。
[49] 日本的軍防令有關府兵資裝自備的內容,和《新唐書》的這段記載略有不同詳參《令義解》,吉川弘文館,2000年,180頁[50] 陳仲安 《唐府兵隨身七事辨》,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183-187頁。
[51] 杜佑《通典》卷一四九《雜教令》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1988年,3820頁[52] 陳仲安《唐府兵隨身七事辨》,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183頁。
[53] 《唐律疏議箋解》,1829頁[54] 《令義解·軍防令》,184頁[55] 池田溫 《中國古代物價初探》,《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中華書局,1992年,459頁[56]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五《人糧馬料篇第六十》,61-62頁。
[57]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卷第二十三《倉庫令·唐2》,2006年,中華書局,第282頁[58] 池田溫《中國古代物價初探》,452頁[59] 關於六馱馬,《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條”,《通典》職官典皆沒有記載府兵備六馱馬的功用,但根據日本《軍防令》記載,六馱馬 “差行日,聽將充馱”,大概是指用於馱運征途糧食資裝。
《令義解·軍防令》,184頁[60]《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五《預備人糧馬料篇第六十》,62頁[61]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讀書班《譯注稿》,《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8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302-303頁。
同參《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289頁[62] 有关唐代马的标准食量,同可参《唐六典》卷一七“典厩署条”,484页[63] 陳國燦《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軍的救于阗之役——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四號墓部分文書的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2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27-35頁。
[64] 杜佑《通典》卷一四九《雜教令》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3821頁[65] 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考》,《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500-518頁;又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211-224頁。
[66] 杜甫《杜詩詳注》,仇兆鼇注,1979年,532頁[67] 杜佑《通典》卷一四九《雜教令》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3823頁[68]《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五《誓眾軍令篇第三十三》,34頁[69]《令義解·軍防令》,吉川弘文館,2000年,189頁。
[70] 有關兵募的研究可以參考菊池英夫《關於唐代兵募性格和名稱》,《史淵》67、68,1956年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歷史研究》1981年第4期楊鴻年《唐募兵制度》,《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張國剛《關於唐代兵募制度的幾個問題》,《南開學報》1988年第1期孫繼民《從武周智通擬判為康隨風詐病避軍役等事看唐代的兵募》,《敦煌吐魯番文書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2000年[71]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13頁。
[72] 參見唐耕耦《唐五代時期的高利貸——— 敦煌吐魯番出土借貸文書初探(續篇)》, 《敦煌學輯刊》1986 年第1期,142頁[73] 錢伯泉《從 考察唐初西域的政治經濟狀況》,《新疆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103頁。
[74]《通典》卷一四九《兵二•雜教令》,3820頁[75]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14頁[76] 同上書,216頁[77] 《王梵志詩校注》卷四,第458、459頁[78] 陳國燦:《唐代的民間借貸——吐魯番敦煌等地所出的唐代借貸契券初探》, 《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 218- 219頁。
后收入氏著《唐代的經濟社會》第六章《唐代的民間借貸》,173頁[79] 趙志超《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士兵借貸問題研究》,《西域研究》 2009年第 2期,49頁[80] 有關帛練的價格參《天寶二年(743) 交河郡市估案》,池田溫《中國中古的物價》,452-453頁。
[81] 《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開列的八個等級絹,最高等級的絲織品產地集中在河南河北541頁[82] 參劉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軍政體制研究》,162頁[83]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16頁。
[84] 《宋刑統校證》,350頁[85] 《王梵志詩校證》,223頁[86] 原錄文為“三”,經仔細辨析圖版當為“二”[87]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23頁[88]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22頁。
[89](美)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35頁[90]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20頁[91] 錢伯泉《從 考察唐初西域的政治經濟狀況》,101頁[92] [美]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31頁。
[93]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229頁[94] 《王梵志詩校注》,588頁[95] 此处解释蒙王素先生提示,专致谢意[96]《王梵志詩校注》卷四,380頁[97]《王梵志詩校注》卷二,215頁。
[98]此字释读应该是“斋”的异体字“ ”参见黄征《敦煌俗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518页此处释读蒙武绍卫博士提示,专致谢意[99]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208頁[100]《王梵志詩校注》卷二,198頁。
[101]《王梵志詩校注》卷一,31-32頁[102] 《北史》卷八〇《胡國珍傳》,中華書局,1974年,2688頁[103] 《王梵志詩校注》卷二《好住四合舍》,201頁[104] “其道士、女道士、僧、尼行道散齋,皆給香油、炭料。
若官設齋,道佛各施物三十五段,供修理道、佛,寫一切經;道士、女道士、僧、尼各施錢十二文五品以上女及孫女出家者,官齋、行道,皆聽不預若私家設齋,道士、女道士、僧、尼兼請不得過四十九人”《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127頁。
[105]《王梵志詩校注》卷一《沉淪三惡道》,60頁[106] 詳參張蔭才《吐魯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幾件唐代文書》,《文物》1973年第10期,73頁本文原載《唐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来源:“吐鲁番文书研究”微信公众号